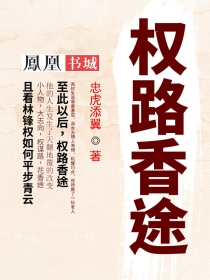孙晓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飞飞小说网www.wonderlifelive.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第七章我本青都山水郎下
崔轩亮毕竟有着内功底子,耳朵远比常人灵敏,这会儿终于给吵醒了。他睁眼来看,惊见面前站着两名中年男子,容貌猥琐,嘴边蓄了两茎长须,背后还负了只大包袱,好似要出远门一般。崔轩亮暴喝一声,赶忙翻身起跳,学着叔叔的架势,厉声道:“来者何人?是不是小偷?”眼看崔轩亮身法利落,虽说是个小白脸,身材却高达八尺以上,双肩开阔,宛如常山赵子龙的形貌。那两人吓了一跳,颤声道:“我们……我们不是小偷,我们是会馆里的人。”
崔轩亮喔了一声,回头去看会馆,果然大门开启,想来这两人真是从会馆里出来的,并非胡言。他稍感放心,便又道:“原来两位大哥是会馆的人,那尚六爷呢?他在不在里头?”
那两名男子互望一眼,眨了眨眼,只见一人拍胸傲然:“哪!我就是尚六爷。”崔轩亮大喜道:“什么!原来你就是尚六爷啊,你方才在做什么啊?怎地都不来应门?”
那“尚六爷”嗫嚅半晌,忽地大咳一声,道:“我方才在午睡,没听到敲门声。”崔轩亮叹道:“是啊,夏日炎炎正好眠,我也睡得香呢……”正自言自语间,却见那两人脚步慢慢后退,来到了岸边,正要急急跳上小舟,崔轩亮却是一个健步抢来,喝道:“且慢!”
那两人魂飞天外,大惊道:“你……你要干什么?”崔轩亮忙道:“我有货要交给你们啊,你们可别急着走了!”那“尚六爷”颤声惶恐:“你……你有货要交给咱们?”
崔轩亮道:“是啊、是啊,您都忘了么?是您托我叔叔带来的货啊,难道你都不要了?”说着开启木箱,示意尚六爷亲自来看。
那两人相顾惊叹:“***……这是铜钱啦……”
炽热的阳光下,满箱铜钱刺眼慑目,想来箱里少说有千贯通宝钱,足抵万两白银。崔轩亮怕人家不肯收,便又打开了其余木箱,却见箱中放着一只又一只青花瓷,其上草书飞舞,或是“江西”,或是“湖广”,全是各地高手匠人烧制而成的精品。
那“尚六爷”望着满满四大车的货,不觉吞了口唾沫,道:“这……这都要给我们么?”崔轩亮笑道:“是啊,咱们费了好大的劲儿,这才运到了‘三山会馆’,您快来点收吧。”扛起了木箱,道,“这货要堆哪儿?”
“堆船上,堆船上。”那尚六爷很是好心,不待崔轩亮慢吞吞来搬,竟也奋力扛起了一箱铜钱。崔轩亮心下大喜,道:“尚六爷,您真好心。连这粗活也肯做。”那“尚六爷”很是随和,忙道:“当然、当然,大家一起出力,那才搬得快啊。”说着朝同伴怒喝,“还愣在那儿做什么,快来帮忙啊!”
铜钱是朝廷的信用,可抵白银黄金,青花瓷更不必说了,南洋东洋尽皆视为传家宝。那“老七”又惊又喜,忙拼死来搬,就怕慢了一点半点。
那海舟舱底宽广,颇能载重,三人齐心协力,不久便把车上的货搬得一干二净。好容易可以交差了,崔轩亮自是呼了一口长气,看这些货品经过千辛万苦,如今总算有了归宿,心下也甚欣慰。便道:“这可行了。尚六爷,我的钱呢?”
“尚六爷”咦了一声,眼珠儿转了转,便伸手到衣襟里乱掏,半晌过后,便取出了一张纸牌,道:“看,这是琉球王的银契,你拿着这张纸进屋,咱们国王便会拿黄金给你了。”
崔轩亮大惊失色:“什么?琉球国王在屋里?”尚六爷笑道:“是啊,咱们国王御驾亲征,现下亲自来了烟岛。一会儿他要是喜欢你,说不定多送一箱金子给你哪。”听得打赏如此丰厚,崔轩亮自是大喜过望,忙拿起了银契,欢天喜地的奔入了会馆,喊道:“草民拜见大王!”
面前空无一人,但见会馆里满是凌乱,柜子倒的倒,抽屉开的开,地下满是纸张,墙上字画也坠落在地,宛然是个废墟。崔轩亮一脸讶异,左右瞧了瞧,喊道:“琉球王!琉球王!我来收钱了,请问你在家里吗?”
他大喊大嚷,四下搜寻,屋里却迟迟无人作声。他满心迷惑,在屋内来回绕行,忽见面前挂着一幅横轴,画大海之景,崔轩亮行了过去,仰望题跋,喃喃地道:“梦海……”
面前是幅《梦海图》,水墨留白,勾勒出海上的云烟雾气,正中一艘小舟,正于狂涛巨浪中疾航,看那笔墨甚是夸大,浪头汹涌翻起,层层叠叠,竟比小舟高上数十倍不止,仿佛群峦叠嶂。崔轩亮自己也曾进过“梦海”,深知这海其实便是“苦海”,若说与“梦”字有何牵连,也只能算是恶梦一场。他越看越觉害怕,忽见图上另有一行诗,忙读了出来。
“羽满高飞日,争妍有李花。真龙游四海,方外是吾家。”
正纳闷间,猛听耳边嗖嗖轻响,似是有人走近之声。他大喜呐喊:“琉球王!”急急转头去看,惊见墙边站了一人,白衣白靴,通体全白,头上罩了个白布套子,乍看去,便与墙壁颜色一个模样,若不仔细瞧,恐怕还认不出来。
崔轩亮大惊道:“琉球王,你……你长得好怪啊。”
白影一晃,竟然从墙上走了下来,便朝窗边奔去。崔轩亮慌道:“琉球王!等等!等等!你还没付钱啊!”说着右手暴长,便朝那白影拉去。
“嗡”的一声,面前精光一闪,似有亮晶晶的东西朝自己射来,看那东西快捷无伦,尚未飞到面前,鼻中便闻到一股腥气。崔轩亮不知这是什么东西,正要伸手去接,忽然背后又是风声劲响,一道绿影飞来,两道影子半空一撞,“哧”的一响过后,那亮晶晶的东西倒弹而出,眨眼间便给震得无影无踪。背后那物却不减来势,撞开前物后,仍朝白影子射去。
“嗡”的一声大响,白影身上散出刀光,护住身遭,那绿影子来势更快,刀光飞影,两相震荡,骤然间纸窗爆开,那道白影倒飞而出,竟给震了出去。地下却传来“当”的一响,似有什么东西坠落。
亮晶晶大战碧幽幽,当真莫名其妙之至。崔轩亮哑然失笑:“好怪啊。”他不知适才自己从生到死,由死到生走了一遭,左顾右盼间,正要去找那白影子,却早已消失不见了,转头去看背后,却也不见人影。正迷惑间,忽见半空中飘落了一道绿影,望来碧森森的,他张掌去接,凝目而观,惊见手中东西不足一钱之重,竟是一片树叶!
崔轩亮吃了一惊,看适才背后射来的东西势如雷霆,快似闪电,岂料竟是这片薄薄的叶子!他呆呆看着,忽见地下还躺了一件东西,好似是从白影子身上掉落下来的。崔轩亮眨了眨眼,忙走过去,俯身将之拾起。
“吱吱呀呀吱吱……”手指触到东西的一刻,四下传来窃窃私语,好似神鬼交谈,随即一股阴风吹入屋内,冰寒森然。
常人若是在此,必定惊惶恐惧,无以复加,崔轩亮却是哈哈笑道:“好凉快呀。”他抖了抖衣襟,通体舒畅,便又低头来看掌里的东西,见是一只钥匙。
寻常钥匙若非生满铜绿,便是满布铁锈。崔轩亮自己身上便带了一串,皆是船上所用,脏兮兮的甚是怕人。可掌中这只钥匙却不见分毫锈蚀,好像新的一样。崔轩亮拿出了手帕,在钥匙上擦了擦,触到钥匙上还刻有字。他低头来看,却见钥匙上写了一行字,字迹小得不成话。他把钥匙凑到眼旁,眯眼辨认,只见那开头三字是“张三丰”,下头另有一行细小怪字,又像是“力”,又像是“乙”,仿佛是东瀛文字,让人瞧不明白。
正讶异间,忽然背后给人拍了拍,登让他大喜回头,喊道:“琉球王!你终于来了!”
背后没有琉球王,却有八个小民,见是老陈、老林、方姓少年与那五名庄稼汉。诸人满面狐疑,全在瞄望自己。崔轩亮眉头紧皱,便伸长了颈子,朝门外去看,喊道:“琉球王!琉球王!你在外头么?”众人一脸惊讶,都不知他在嚷些什么。老陈咳道:“少爷,你怎么进屋来了?那些货呢?”崔轩亮笑道:“那些货已经运走啦。”
众人寒声道:“运走了?”崔轩亮忙道:“是啊、是啊,方才你们吃饭的时候,尚六爷便出来了,他把货搬上了船,便驾船走了啊。”老陈、老林吞了口唾沫,心下都有不妙之感,他俩朝屋内望了望,颤声道:“那……那货款呢?”
崔轩亮赶忙取出了纸牌,道:“收到了,收到了,看,这是尚六爷给我的银契。”
众人急急围拢过来,各朝那“银契”去看,只见纸牌上写了几个东瀛字,见是“京都烟花馆符切,票抵……一次。”
“少……少爷……”老陈双眼突出,老林全身寒,两人面面相觑,牙关颤抖,忽又想起一件要紧事,颤声便问:“等等,那……那包黄金呢?”
崔轩亮“咦”了一声,这才惊觉自己身轻如燕,他兜兜转了个圈,看遍全身上下,那包黄金竟也不翼而飞了。老林、老陈对望一眼,顿时膝间一软,跪跌在地,大哭道:“完啦!全完啦!遇到贼人了!整整赔掉十万两白银啦!”
崔轩亮皱眉道:“等一等,你们……你们说尚六爷是贼么?”老陈大哭大吼:“少爷!你还没弄懂么?你遇到的不是尚六爷,你遇到的是骗子啊!”
“哎呀”一声,崔轩亮飞身跳起,这才知道自己遇到坏人了,看满船货物给人骗得精光,非但赔光了二爷的本钱,怕连回中原的盘缠也没了。老陈、老林抱头痛哭,崔轩亮更是倒在地下,挥手舞脚,放声大哭起来。
那少年小方本还等着收钱,可人家才给拐掉了全身家当,怕已痛不欲生,自己若选在此时催收车款,难保不给人围殴致死。无可奈何间,只得杵在一旁,等候收钱良机。
众人哭得呼天抢地,忽听门口传来说话声:“你们是什么人?为何闯进凶宅?”
听得“凶宅”二字,众人一齐转头去看,只见会馆门前走进了一批人物,人人手上提刀,身穿劲装,胸前都绣了一只白云燕儿。为之人则是空手,身上罩着一件厚重斗篷,衣襟上绣着一只红雀儿。虽在大热天里,却也没见他出什么汗。
烟岛共有十二位教头,人人武功精强,手段利落,向来是岛上执法。老陈知道救星来了,忙跪地大哭:“大爷!大爷!咱们的货给人偷了,您快帮忙抓贼啊!”那斗篷男子急忙上前,搀扶道:“老丈别慌,您有话慢慢说,莫要行此大礼。”
老陈擦拭泪水,抽抽噎噎地道:“咱们……咱们是商人,有批货要交给尚六爷……岂知……岂知会馆里居然藏了骗子……”
想到船货全给拐骗一空,众船夫家中却是老的老、小的小,全都等着吃,二爷从此积欠数万两巨款,老陈、老林心下一酸,忍不住又号啕大哭了起来。
崔轩亮也是频频拭泪,哭道:“是啊!是啊!那两人是从会馆里出来的,又说自己是尚六爷,便把我车上的东西给搬走了……”那斗篷男子年约三十来岁,肤色黝黑,神情干练。他闻言蹙眉,道:“我已在门上贴了封条,提醒各方来人注意,你们都没瞧见么?”
老陈、老林心下一凛,这才想起门上贴着符印,上书“公务重地,严禁擅闯”这八个字,原来便是封条之意。崔轩亮抽噎道:“我……我不知道那是封条,反正……反正他们是会馆出来的,我也没想那么多,便陪着搬货了。”
众汉子愕然道:“你还真好心啊,难不成你只顾着搬,都不问他们收钱么?”崔轩亮抽噎道;“有啊,他们……他们不是拿了那张纸牌给我,说可以找琉球王换钱……”
“琉球王?”众人微微一愣,那斗篷男子接过纸牌一看,沉吟道,“那两人可是面色蜡黄,嘴角蓄着两茎长须么?”崔轩亮哭道:“对对对,他俩还负着大包袱,像是要出远门……”
那斗篷男子稍稍看过了纸牌,心下已有定见,便道:“这两个是张党的人。”老陈讶道:“张党?那是什么?”那斗篷男子解释道:“‘张党’是海盗,贼众皆是汉人。只因他们过去是张士诚的部众,便给咱们统称为‘张党’。”
老陈愕然道:“张士诚?就是和太祖打过仗的那个张士诚么?”
那斗篷男子颔道:“就是他。这张士诚战败后,部下却不肯降伏,于是都逃到了鬼海中,聚众造乱。后来日本的‘荣之介’鬼海,便将他们的领杀死,将残部收编旗下。”
老林颤声道:“荣之介,这……这家伙不就是倭寇的大头目么?”那斗篷男子道:“没错。现下‘张党’的人已成倭寇向导,专替匪徒带路,来劫夺自己的汉人同胞。”
听得世间竟有如此汉奸,众人义愤填膺,自是骂不绝口。老陈苦笑道:“怎么搞的?这倭寇过去从没胆子来到烟岛啊?怎地张党的人竟会……竟会……”
那斗篷男子叹道:“说来真是对不住了。敝师今年六十大寿,各方宾客云集,咱们也不好盘问宾客的身份,是以三教九流都来了。为此岛上乱成了一团,咱们上上下下都忙得不可开交。”听得“敝师”二字,老陈不由“啊”了一声,忙道:“您……您是魏岛主的徒弟么?”
那斗篷男子淡然道:“是,在下行四,人称‘林唐手’便是。”老陈、老林听得“林唐手”三字,不觉“啊”了一声,立时想起那位带艺投师的琉球舵头,忙道:“原来是魏岛主的四弟子林思永,失敬,失敬。”说着打躬作揖,十分礼数。
“唐手”是琉球武术,源于中土,便如琉球国宝三弦琴一般,也是经浙闽一带传入岛内,数代沿袭下来,渐成琉球国技。不少东瀛人亦慕名来学,又因东瀛语中的“唐”、“空”二字读来同音,久而久之,积非成是,终给称为“空手道”。
琉球唐手、朝鲜新罗掌、中原铁砂掌,均是以外门硬功闻名,这林思永本名“林丸玉”,乃是琉球人士,也是个空手名家,故有“林唐手”之称。只是他来到烟岛后,曾见识过魏宽的身手,大惊之下,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也才明白自己无论怎么习练唐手,若少了内功调和,终究有所不足,于是便拜魏宽为师,学习道家吐纳之法。又因他拜师时年已二十五岁,是以年纪远比其余弟子为大。
崔轩亮喃喃地道:“林……林大哥,那些人还没走远,你……你可不可以替我去抓人回来?”林思永道:“当然,份内之事,林某自该为诸位办到。”当下转过头去,吩咐下属道,“即刻备船,分两面追缉张党,一有消息,即刻回报。”
几名下属大声答应,疾疾奔出,竟无一人推诿,想来烟岛的官差很是不同。崔轩亮见这些人武功不高,怕还打不赢自己,便又问林思永:“林大哥,你自己不去抓人么?”
林思永摇头道:“对不住,在下有要事在身,暂时走不开。”老陈微微沉吟,看这林思永面色烦闷,料来与此间情事有些干系,忙道:“林公子,这会馆究竟怎么了?为何封了起来?”
林思永叹道:“实不相瞒,尚六爷过世了。”众人大吃一惊:“尚六爷死了?他……他可是琉球巨子啊!他是怎么死的?”林思永叹道:“他是病死的。”众人心下更惊:“病死的?可是一个月前他……他还捎信过来了啊,怎么一下子就死了?”
林思永道:“尚六爷的病来得很快,听说他里神志不清,了高烧,午夜时找了大夫看诊,结果不到天亮便死了。”
这位尚六爷本名“尚忠志”,乃是琉球王国的大人物,长年于烟岛经商,此番若是暴病而卒,定是轰动琉球的大事。老陈颤声道:“他……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这般厉害?可是中风么?”
林思永摇头道:“不晓得,反正咱们这几日都派人来此把守,以免闲人误闯进来。”
崔轩亮喃喃地道:“派人把守?可是……可是咱们方才到会馆敲了半天门,都没见人出来应答啊……”林思永目光向后一撇,一名下属低声道:“启禀四少,这……这会馆里不大干净,咱们……咱们不敢守在屋里,所以才……才……”
老陈悚然一惊,忙道:“不干净?什么意思?”林思永咳了一声,便朝属下使了个眼色,道:“少说两句。你们去屋里点一点,看看少了什么东西。”
一众汉子唯唯诺诺,忙走到了屋子里,正要翻找搜查,却听林思永又加了一句嘱咐:“记得拿艾草熏一熏,尤其别碰尚六爷房里的东西,知道么?”
眼见众汉子胆战心惊,自在那儿点燃艾草,四下熏烘,老陈、老林看在眼里,不由浑身抖,已知“三山会馆”里何以人去楼空,颤声便问:“林……林公子……这……这尚六爷怎么死的?可是……可是瘟……瘟……”
也是他俩内心害怕,“瘟疫”二字临到嘴边,却迟迟说不出口,林思永自知隐瞒不过,便道:“尚六爷确是有些病症,可能是外感所致,不过岛上已然有备,诸位无须惊慌。”
这安慰话一出,众人反而更是怕得抖,老林低声道:“林公子,咱们也进屋子里了,可会染病么?”林思永安慰道:“放心吧,你们瞧我这几日都守在屋里,不也没生什么病么?诸位切莫危言耸听,到时闹得岛上人心惶惶,那可不美了。”说着取出了一瓶丹药,一人上一颗,道,“你们若还担忧,便把这药吃了,有病祛病,无病强身。”
老陈见那药丸味道辛辣刺鼻,想来能去除瘴气,忙把手一仰,囫囵吞了。老林、崔轩亮也是吓得魂不守舍,也各服了一颗。林思永又道:“还有人想吃药么?都过来吧。”
屋内除开老陈、老林,另有那五名驾车汉子,众人诚惶诚恐,登时过来排队领药,崔轩亮怕一颗没用,便又排到队伍最末,等着多吃几颗。
正排队间,忽听一人道:“几位老板,你们可以付钱了么?”
众人回头去看,却是那方姓少年过来要钱了。这人倒是豁达生死,屋内虽有瘟疫,也是蛮不在乎,想是个要钱不要命的。老陈苦着一张臭脸,看此行赔得倾家荡产,可这车资却不能少付一点半点,他掏出了碎银,正要付钱,那林思永却拦了过来,道,“且慢,他收你多少钱?”老陈忙道:“咱们跟他要了五辆车,一两八钱银,兼带上下货。”说着又问林思永:“这……这价钱还行吗?”
林思永瞧了瞧那方姓少年,道:“还行,你付钱给他吧。”
老陈如数付了钱,那小方点了点银两,便又分给了众车夫,登作鸟兽散了。
眼看那方姓少年走远了,那林思永却还凝视着这人的背影,若有所思。老陈忙道:“林公子,这小子是坏人么?”林思永叹道:“坏人也称不上。只是这少年做生意一向不老实,时常诈欺生人,不知闹出了多少纠纷。你们下回遇上了他,最好提防点。”
老林悚然一惊,忙道:“等等……莫非……莫非这孩子也是‘张党’的人么?”
众人越想越惊,看那两个骗子现身的时机极巧,说不定真是那方姓少年的同伙也未可知。老陈、老林慌了起来,林思永却道:“放心吧,这小方虽不是守规矩的人,可碍在父母的面上,却还不至于作奸犯科。否则早给我扣押起来了。”
崔轩亮道:“林大哥,这小方家里还有什么人啊?”林思永道:“这小孩家里人可多了,全住在岛西的‘方家集’。”崔轩亮愕然道:“等等,‘方家集’?这岛上有许多姓方的么?”
林思永道:“没错。方姓是岛上汉人第一大姓,少说有两千余户。”
崔轩亮吃了一惊,他昨夜曾听天绝僧提起,说他要找一户方姓人家,可如今听来,这烟岛上姓方的却似成千上万,不知天绝僧要从何找起了?他喃喃又道:“林大哥,这岛上姓方的人,可有什么来历么?”林思永道:“故老相传,岛上方姓之人,全是方国珍的后代。”崔轩亮喃喃地道:“方国珍?这又是谁啊?”林思永道:“方国珍也是割据群雄之一,据说他投降洪武帝后,几名部属心存不满,便驾船出海,来到烟岛定居,算是第一批抵达此地的汉人。”
老陈详熟开国史事,自知这方国珍与张士诚一般,至正年间都曾割据江南,只不过方国珍出身海盗,才干远不及群雄,一待陈友谅、张士诚等人相继身死,便急急向太祖乞降,盼能苟全性命。想来他的部众不耻其所为,这才远避海外。
想起方国珍是浙江黄台人,老陈连连颔:“原来这孩子是方国珍之后,难怪自称是浙江人。可他怎么又说祖上曾在南京为官?”林思永摇头道:“这就不晓得了。你若想打听他的生平,不妨自己去岛西走一遭。”
区区一个苦力少年,谁有心思多问他的来历?老陈担心屋子里不干净,只想早些开溜,便道:“林四爷,左右无事,咱们可以告辞了吧?”林思永道:“当然。不知诸位高姓大名,船泊何处,这便留个口信下来,我若找到了各位的财货,自会差人通知诸位。”
老陈感激涕零,拱手道:“多谢公子高义。敝姓陈,这位姓林,咱们的船便泊在岛北的庚午埠,您一来便知。”林思永虽神色疲困,还是吩咐下属记下了。
这烟岛过去借着魏宽的威名,居民向来夜不闭户,从无贼匪敢犯。孰料一场六十大寿办下来,岛上却接连生了这许多事端,想来林思永来回奔波,这几日必是累坏了。
众人不敢久留,正要朝门口而去,却听屋外脚步声响,听得一个苍老的嗓音道:“这就是现场了么?”一名女子道:“是,请上官哥这边来。”
眼看又有人来了,老陈忙带着崔轩亮避在路旁。但听脚步声响,当前走进了一名老者,色银白,宽袍大袖,身材略嫌矮小,两条手臂却是魁梧粗壮,满布青筋硬肉,极是孔武有力。
练家子现身而至,崔轩亮悄悄来到门边,正想脚底抹油,忽然鼻端闻到一股香气,随即眼前一亮,婀婀娜娜走进了一个大美人。
她约摸三十来岁,穿了身娇翠花绸短袖,露出了半截晶莹玉臂,看她腕上还有一只翡翠镯子,色泽葱绿,极显名贵。只是崔轩亮什么都没瞧见,只是张大了嘴,浑身抖,直盯着人家的那双漂亮眸子,口涎横流。
崔轩亮不是没见过女人,家中的两个堂妹、船上的小茗、小秀,都算是美人儿。可要说到谁的眼睛漂亮,却没人比得上眼前的凝眸慧眼。
那双眼睛皎洁明亮,楚楚动人,带了一抹天生的俏皮风流,尤其顾盼之际,眼波才动,种种心思灵巧,全都倾泻而出,任谁给这双眸子瞧了,都要心里怦怦直跳,神思不属。
二人四目相交,那双眼儿先是眨了一眨,带了几分惊讶,想是没料到会在此撞见一个英俊少年,随即微微侧让,略显羞涩,当是没料到这人会这般无礼,只管死盯着自己。
崔轩亮呆呆注视那双美眸,心头越火热,情不自禁间,竟然凑过头去,便朝那双美目去吻。说时迟,那时快,那双美眸冒出了熊熊怒火,但听“啪”的一声大响,崔轩亮只觉天旋地转,脚步一个踉跄,便已摔跌在地,昏晕过去。
“丸玉!”那美女叉腰怒喝,“这是怎么回事!屋里怎会乱成这模样?有谁来过了?”
那林思永赶忙上前,急急躬身:“适才‘张党’的贼子入屋行窃,咱们弟兄一个不备,便给他们盗走了一些事物。”
那女子长得风流,可一旦板起脸来,却有种说不出的威严,听她沉声道:“张党?”嗓音略略一提,似想大雷霆了,可目光一瞥,却又见老陈、老林浑身抖,躲在一旁害怕,便又压下了火气,指着地下的崔轩亮,道,“这少年又是什么人?不会是张党的匪众吧?”
林思永忙道:“不是,不是。这些人是中原来的客商,适才一个不巧,也给张党的贼子了财物,损失不少。”那女子瞧了瞧老林、老陈,沉吟道:“中原来的客商,他们姓什么?”
林思永恭恭敬敬地道:“回师娘的话,他们自称姓陈,船就泊在岛北。”
听得“师娘”二字,老陈自是愣住了,看那女子明明与林思永年岁相仿,却不知什么缘故,竟成了人家口中的“师娘”,当真奇哉怪也。他心思略转,登时想到了一人,忙拉住了老林,附耳道:“快走,快走。”
老林也认出人来了,满心害怕间,便与老陈协力抱起少爷,正要夺门而出,却听那女子朗声道:“两位且留步,我一会儿有话问你们。”
号令一出,门口便站上了两名武功汉子,双手叉腰,冷然道:“诸位请回吧。”老陈、老林叫苦连天,只得在一旁乖乖站好。至于一会儿要打要杀,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那女子见留下了人,便不急于上前盘问,只转过身去,自向那银老者道:“上官哥,上官哥,说来真是难为情,您一来烟岛,便得劳您走这一遭……”那老者道:“别说这些见外话,大家过去都为皇上效力,血浓于水,魏宽的事情,便是我上官义的事情……”
听得“上官义”三字,老陈心下一凛,只觉这名字很是耳熟。他细目打量那老者,只见他个头不高,两条臂膀却是雄健粗壮,想来练了极厉害的外门硬功。老陈“啊”了一声,心下恍然,已然想起此人的来历。这老者不是别人,正是当年“燕山八虎”之一的“地虎”上官义。
“铁棒”孟中治、“立马刀”郭奉节、“壁虎”丘重、“地虎”上官义……并同排行第一的“飞虎将”崔风训,便是当年的“燕山八虎”。这上官义其实也不矮,可当年军中同袍动辄身长**尺,便总戏称他为“地虎”,便如水浒里的王英。只是上官义处事平和,少与人纷争,永乐帝喜欢他的沉静,便将他调入提刑按察司,统辖“三法司”五千名官差。永乐朝后,他便转做镖局生意,没想会在此地撞见他。
这上官义既是提刑按察使出身,想来此番来到现场,定是要借他的本领查案。正想间,上官义已自行问向林思永,道:“林贤侄,财物清册做出来了么?”
林思永忙走了过来,便从怀里取出一本册子,恭恭敬敬奉给了师娘。那女子接过了,便又转给那名老者,道:“屋内大小物事都列在这儿,请上官哥过目。”
那女子真是看小不看大,明明一本册子奉上,却还得多上一手,弄得繁文缛节也似。上官义朝林思永笑了笑,便接过了册子,一页一页翻动。过了半晌,便道:“这不是劫财杀人,珠宝饰都在。”
听得此言,众人才知那老者是来查案的。又听那女子淡淡地道:“没错,值钱东西没少,若非如此,怎会把张党的小偷给引来了?”说着便朝林思永等人瞥了一眼,目光颇见不悦。
林思永急忙躬身:“师娘息怒,窃案频出,治安不靖,全是丸玉的错。请师娘重重责罚。”
那女子淡然道:“你不必来套我的话。等你师父出关之后,自会出手罚你。”那林思永原本英风爽飒,可来到那女子面前,却无端矮了一截,给师娘冷冷数落了一顿,也只能频频哈腰,不敢作声。
正说话间,那上官义已在屋中转了一圈,大略看过了陈设,便道:“尚忠志死的时候,屋里还有什么人?”那女子冷冷地道:“丸玉。”
林思永听得吩咐,这才敢上前说话:“回前辈的话。尚六爷死的当晚,身边共有两名武功随扈,除此之外,会馆里另有八名下人。他们还请了一名大夫,整夜看顾他。”
上官义点了点头,道:“我听你师娘说过,尚忠志好像走的很快,可是如此?”
林思永道:“师娘说得话,当然是没错的。据说尚六爷傍晚烧,午夜病,未及黎明,便已断气。会馆里请了大夫过来整治,却也看不出病因。”
上官义皱眉道:“听说尚忠志还是个练家子,对么?”林思永道:“正是。这尚六爷今年五十七岁,乃是我琉球唐手名家,身体硬朗,平日没病没痛,然则烧之后,却撑不到一晚便死了。”那女子插话道:“这尚忠志可是中了毒?”
上官义沉吟半晌,道:“林贤侄,你验过尸了么?”林思永摇头道:“没有。尚六爷是琉球巨子,身分非比寻常,咱们不敢擅自作主,须等琉球王的使者到来,方能剖尸勘验。”
上官义道:“这是你师娘的主意么?”那女子俏脸一沉,道:“是又如何?上官哥有何指教?”上官义咳了几咳,什么指教都没了,道:“没什么,只是……只是这几日天气热得紧,这使者若是到迟了,恐怕尸有变。”
林思永道:“此节不劳前辈担忧,琉球使臣明日便到。现下尚六爷的遗体用石灰掩着,放在岛南下风处。应能撑个一天。”上官义道:“等等?你用石灰掩盖他的尸身?还放在下风处?”林思永咳了几声,颔道:“正是如此。”
上官义嘿嘿一笑,想来瞧到了什么,当即道:“林贤侄,当晚给尚忠志诊断的大夫呢?你可否带他过来见我?”林思永咳了一声,道:“对不住,那人已经不在了。”
上官义脸色微变:“不在了?怎么,难道这人潜逃了?”林思永道:“不,这位大夫也死了。”众人都是大吃一惊,上官义也深深吸了口气,道:“死了?怎么回事?”林思永叹道:“尚六爷是黎明时候断的气,到得当天下午,他的两名武功随扈,并同夜里给他看诊的那名大夫,也都相继过世。”
听得此言,老陈吓了一跳,老林也是牙关颤抖,这才晓得瘟疫已然传开了。上官义嘿了一声,道:“这几人的尸体都验过了?”
林思永摇头道:“没有。事情太怪,没人敢拿性命来试。现下这几人的尸身已然烧化了。现今唯一的线索便剩这处凶宅与那尚六爷的尸身,盼前辈拨冗指点。”
石灰可以防腐,却也可以杀毒。看这尸体用石灰掩盖,想来这案子压根儿便是瘟疫,哪里是什么命案?上官义有些恼了,当即道:“你师父呢?他知道此事么?”
林思永看了那女子一眼,待见她点头允可,方道:“回前辈的话,在下尚未将此事禀于家师。”上官义皱眉道:“贤侄,不是我说你,你师父何等的大人物?什么阵仗没见过?生这等怪事,你为何不跟他说?”林思永咳了一声,道:“一来家师正在闭关,二来他过几日便要做寿了,不便沾染这些血腥事。也因如此,师娘才请了前辈过来探查。”
话到口边,那女子又“嘿”了一声,那林思永赶忙改口道:“是、是,请前辈来此,是小人的意思,是小人的意思。”上官义不知他们在搞什么名堂,一时也懒得多想,只双手叉腰,摇头道:“弟妹,我以前是旗手卫都统,管的是京城治安,可不是医药治病。你真确定尚忠志不是染了急症?”
那女子道:“上官哥,我若没有十成十的把握,岂会劳驾你亲自过来?”上官义叹道:“妇道人家的把握,我可没把握。”那女子俏脸一沉,道:“瞧好了,妇道人家的把握,尽数在此。”说着从怀里取出一颗木珠,屈指轻弹,便朝上官义射了过去。
木珠飞出,满室生香,连着平飞了数丈,来势快捷无伦。上官义吃了一惊,正要探手来抓,那珠儿却向下一沉,居然稳稳坠到了他的衣袋中,准头之佳,世所罕见。老陈、老林正要高声喝彩,那女子却举起手来,冷冷地道:“不必。”
那女子刻意展露武功,意在压住屋里男子的气焰,至于这些无聊奉承,自也双手奉还。那上官义吞了口唾沫,也有些怕她了,便从衣袋里捡出了那颗木珠,才拿了出来,鼻中便闻到一股浓冽香气。他微起愕然,道:“这……这是……”
那女子道:“这是辟邪珠。此物去邪怯病,据说佩戴者百毒不侵,蛇虫瘴气皆不能近,我这几日佩着这颗珠子,连头疼的老毛病都好了。”听得这木珠如此神效,上官义自是微微一奇,道:“此物与尚六爷有关?”
那女子淡然道:“上官哥还不懂么?这珠子是尚忠志的遗物啊。”上官义愕然道:“你……你是说,尚忠志平日都佩戴这颗珠子?”那女子冷冷地道:“丸玉。”林思永一听召唤,立时躬身走上,道:“回前辈的话,这辟邪珠是在一处抽屉里找到的,尚六爷平日是否佩戴此珠,晚辈不敢断言。”上官义皱眉道:“这可怪了。这宝珠如此神效,他该日夜随身佩戴才是,怎么会取下来?莫非……莫非……”
众人眼神相交,已知事有蹊跷,尚忠志既有宝珠在手,为何不随身携带?莫非府里有人上下其手?可既有人存心不轨,为何不将之盗走,却任凭这宝物留在府中?莫非是怕事机败露不成?老陈、老林对望一眼,都觉得此事另有玄机。
上官义沉吟半晌,他把玩着那颗木珠,道:“弟妹,这辟邪珠天下罕有,尚忠志是打哪儿弄来的?”那女子道:“你把珠儿放到阳光下,答案自然分晓。”
上官义拿起宝珠,朝窗边走近几步,阳光耀眼刺目,霎时映得宝珠灿烂生光,但见珠儿上清清楚楚刻着三个字,见是“张玄玄”。上官义大吃一惊,失声道:“武当张三丰!这……这是张真人送给他的?”
那女子道:“应该是,不然这珠儿为何刻着张三丰的名号?”
张三丰神龙见不见尾,传说此人早已过世,却又有人说他已飞升成仙了,连永乐帝六次遣使上山,却也没曾找到他,倘使这珠子真是张三丰亲手所赠,那便是说这位老道其实早已离开了中原。若非如此,他却是怎么认得这位“尚忠志”?
上官义点了点头,道:“这事确实怪得可以。好,这案子便包在我身上了。这尚忠志若是他杀,决计瞒不过我‘上官地虎’的眼睛。不过弟妹,我丑话也先说在前头,这位尚六爷若真是染病死了,你可得另请高明,否则到时瘟疫四散,做哥哥的可担当不起。”
那女子道:“放心,此事我早已有备。”上官义哦了一声,道:“怎么?你还请了名医助阵?不会是北京的袁神医吧?”
那女子微笑道:“那倒不是,这回来得是袁神医的死对头,王鬼医。”
上官义吃了一惊:“‘鬼医’王魁来了?怎么?他也是来拜寿的?”那女子笑道:“那可不敢当。我差人打听过了,这王魁此番过来烟岛,是为了皇上的龙体。”
上官义讶道:“皇上?”那女子道:“他是搭着‘宣威舰’来的。”听得此言,上官义登时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是给皇上采药来着?这么说来,白璧暇那小子也来了?”那女子淡淡地道:“没错。我昨儿已和白大人见过了面。现下他的舰队便停泊在岛南。”
上官义嘿嘿笑道:“弟妹,这白璧暇千里迢迢而来,想必公务之外,定还有什么私务吧?”那女子皱眉道:“上官哥说话可难懂了,什么公务私务?我魏家与他白大人有何牵扯?”上官义微笑道:“弟妹何必装糊涂?那白云天苦恋令嫒未果,早已哄传江湖,你都不可怜可怜他么?”
陡听飞来横祸,老陈、老林自是魂飞天外,那崔轩亮尚还昏晕在地,殊不知碗里最大块的肥肉已给悄悄叼走。恐怕醒来一看,又要号啕大哭了。
上官义笑了几声,还待要说,那女子却已闭目俨然,道:“上官哥,琉球王的使臣明早便到,到时人家问起案情,我却一问三不知,那可难看得紧了。”上官义歉然道:“是了,是了,咱们少说闲话,办正事要紧。”说着转望林思永,道:“林贤侄,劳驾你陪我查一查屋内,弟妹,请你在此稍候片刻,我女儿女婿一会儿便到,我的吃饭家伙全在他们那儿。”
那女子道:“上官哥去忙吧。这儿自有我来打理。”说着走到老陈、老林面前,微笑道:“过意不去,耽误三位的时光,来,先请坐下吧。”
这女子先前一派威严,指挥若定,此刻却轻声细气,与老陈、老林好言相向,两名老头呵呵干笑,眼光全望着地下,不敢与之相接。那女子笑了一笑,便俯身下来,望向了崔轩亮,轻声道:“,,你还好么?”
崔轩亮先前挨了一记耳光,早已昏迷过去,此际听得柔声呼唤,宛如仙籁入耳,天女降临,便迷迷糊糊地道:“谁在叫我啊?”那女子微微一笑,便将他抱了起来,枕在自己的腿上,捏了捏他的人中。
那女子显有武功在身,内力似也颇为深厚,功力到处,登让崔轩亮悠悠醒转,他睁眼一看,眼前一双纤纤玉足,三寸金莲,便在眼前三寸之地,鼻中一嗅,更得玫瑰芬芳,霎时转头急看,先见了柳叶花裙,肩头一碰,又触温香软玉,崔轩亮张大了嘴,方知自己竟是躺卧在一名美女的怀中。
崔轩亮又惊又喜,又慌又怕,大喊道:“我……我已经死了么?”咯咯娇笑响起,崔轩亮抬头急看,却又见到了那双美眸,他“吓”地一声,急急捂脸坐起,逃到了老陈的脚边,颤声道:“别打我,我不敢了,不敢了。”
先前意乱情迷,去吻这双星眸的主人,顿给打翻在地,不醒人事。此刻梦中醒来,再见这双美眸,自如见到狮虎怒目,让人胆战心惊。那女子见他缩头低手,便又笑了笑,道:“放心,有我在这儿,谁敢打你?”
崔轩亮怯怯望地,可听这声音颇为悦耳,便又悄悄抬起眼来,打量着人家。
直至此时,崔轩亮才第一回见到人家的容貌,只见面前的姊姊年纪不轻,约摸三十来岁,生了一双星眸大眼,若神若电,尤其那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更让他满面通红,便又低下头去,不敢作声。
那女子微微一笑,伸手抚了抚崔轩亮的额,柔声道:“,你们是打中原来的吧?”
姊姊声音温柔好听,还伸出玉手,摸了摸自己,崔轩亮精神复振,立时暴吼一声:“对!”还没来得及详细作答,老陈却抢先了一步,赔笑道:“是、是,咱们……咱们是打泉州来的,敝姓陈,那位姓林……那位小兄弟是咱的……咱的小侄子……”崔轩亮咦了一声,不知自己何时改姓“陈”了,正要出言询问,老林却扯住他的衣袖,示意他莫要作声。
更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