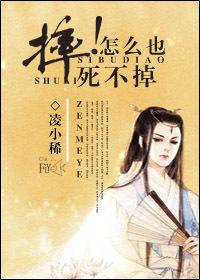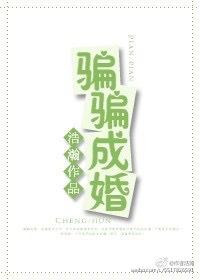玛丽苏女神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飞飞小说网www.wonderlifelive.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直到后来也没有人知道,在波塞冬生日宴会的第二天,我曾偷偷去过一次亚特兰蒂斯。
披着哈迪斯的隐形斗篷,我在欧奈罗宫一路穿梭,几乎是闭着眼睛都能找到那间海底寝殿。仿佛记忆已深深铭刻在骨血里……那熟悉的,遥远海面照落下来的柔和星芒,摇曳在珍珠色地面的粼粼波光,沉厚的金色大门将这影与梦交织的世界与一切喧嚣隔绝。
寂静的,空旷的,只剩时光错肩而过的声息。
我推开门,静静伫立在大殿尽头,眼前一切旖旎宛如一场睽违经年的华梦……直到,看到他。
是在那样幻觉般的曦泽中,亚特拉斯正抱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他双手小心翼翼托起婴儿柔软的小胳膊,无比骄傲地稳稳高举过头顶。婴儿毛绒绒的金色碎发似蒲公英随风起落,一双蓝紫色大眼睛更胜过任何完美无瑕的宝石。
这真是个过分漂亮的孩子,最重要是,和他很像。
婴儿粉嫩的小手乱挥着,奶声奶气的笑声回荡在空阔殿堂里。亚特拉斯眯起眼睛,一边看着他,一边跟着他偏头微笑……
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一个父亲注视着儿子的目光,可以这样温柔。
我的小少年,我的恒星,他有孩子了……那是属于他的血脉,他的骨骼,他的小小复刻。
原来生命的传承是这样奇妙,而又微微令人感到心酸。
站在透明的空气里,我很用力很用力地捂紧嘴巴,才能强迫自己不发出一丝声音。
……
…………
后来,亚特拉斯的千里传音器亮了。他不得以放下婴儿,又温柔地哄了几句才按下通话键,快步走出去。
我犹豫片刻,脱下隐形斗篷,走上前去。
他就躺在小小的摇篮里,身上有一股浓郁的奶香味。一点也不认生,眨巴着那双几乎占一半脸大的眼睛好奇地盯着我,嘤嘤呀呀地叫唤着,伸出肥嘟嘟的小手试图触碰我的脸。
我学亚特拉斯的姿势把他抱起来,高举过头顶。
小家伙咯吱咯吱笑得特别欢畅,双腿在半空中欢快地乱蹬着。虽从未为人父,但那一瞬间,我却好像忽然体味了亚特拉斯的心情……迫不及待地想看他长大,幻想着他长大后的样子,他的眉眼像谁,他的脾气像谁……
我情不自禁眯起眼睛,跟着他一起偏头微笑。
门就在这个时候吱呀一声开了。
我懵了一下。
所有的所有前因后果解释开脱,根本来不及思考。几乎是下意识地抱着孩子缓慢、僵硬、转身。
——他,亚特拉斯,就站在离我三米开外的距离。
这个我思慕了一百年的面容,有一点错愕,有一点慌,又有一点让人心酸的悲伤。像我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拉起他的手宣读誓言时那样,又像他背着昏睡的我回神殿路上连绵不绝的暮雨那样……
在我的记忆里,他好像永远停留在少年时期的模样。
可是怎么我的小少年就高过了我许多,可是怎么,我的小少年就都当爸爸了……
神不会随光阴的流逝而衰老,可这一瞬间,我却觉得,我们已经很老很老了。
星辰遥远散漫,幽幽的月光透过粼粼的海水落入大殿,仿佛一盏柔和的冰蓝色壁灯。亚特拉斯就站在所有光源的汇聚处,像一尊精致到无可挑剔的雕塑,一动不动。
有种隔世的错觉,恍恍惚惚间我们好像已经度过了几个世纪。
“咿——呐——呐”
一声婴儿奶声奶气的呓语将我拉回现实,我转身,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回摇篮。他扯住我的一缕头发把玩,不肯松手,咿咿呀呀地冲着我笑。趁这个空当,我深吸一口气。
准备了一百年,练习了一百年,再次见到他该如何面对,但还是一瞬间就全部土崩瓦解。
亚特拉斯没有走上前来,我知道,他是在等我转身。
我把发丝从婴儿手中轻轻抽离,努力扯出一个微笑,转身,却正好看到奥兰斯敲门进来。
他看到我先是一愣:“普瑞尔……不,珀罗普斯殿下……”奥兰斯看看我,又看看站在门边一语不发的亚特拉斯,最后还是转回我的方向:“您、您怎么在这里?”
我不知如何作答,只能尴尬地不停整理着斗篷的风帽。
奇怪的是,亚特拉斯也没有回答奥兰斯。地板上他的倒影晃了晃,不知道是不是灯光的缘故,它朝我靠近了一些,但是很快又安静下来,在离我只有一步距离的位置。
我有些心酸,不自觉朝前走了一步,站到他的光影之中。
奥兰斯善解人意地轻咳了一声:“陛下,这是今天要处理的公文。”他把一大叠印着蓝色纹章的羊皮纸卷筒搁置在亚特拉斯的办公桌上,然后,非常体贴地对我说,“珀罗普斯殿下,不介意和臣下出去走走吧?”
我十分感谢奥兰斯这百年未变的聪颖细腻:“当然不!”
他微微侧一□,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我轻舒一口气,与亚特拉斯错肩而过,快步走出了繁星殿。
……
亚特兰蒂斯的夜晚其实已经和千年前大不相同。
充斥在城市每一个角落的喧嚣声破坏了当初的宁静安详,波塞多尼亚已经是继派朗城之后,举世闻名的第二个不夜城。
不同于派朗城日夜不分的忙碌生产,这里的夜晚是年轻男女狂欢放纵的仙境——磁欧石点缀的霓虹灯胜过了星光的璀璨;数千座高低不等的金圆顶建筑通夜明亮;狄奥尼迦亚码头昼夜不停地运载货物,五层楼高的巨型船厂里灯火通明喧嚣震天;数百个大中型购物市场二十小时不间歇营运;以弗克街为首的几条娱乐大道几乎能将歌舞声传到奥林匹斯。
奥兰斯带着我走过几条标志性大街:“殿下,您看现在的波塞多尼亚是不是变了很多?”
身边不时有呼啸而过的马车,不同于珀罗普纳索斯的是,这里一尘不染的大理石街面不用担心马车溅起的泥浆弄脏衣服。路边有吟游诗人弹奏着里拉琴,哼唱不知名的歌曲,他脚下放了一顶破烂的帽子,里面是零零碎碎的几枚派朗。
“是的,这里的变化超出我想象。”我由衷地说。并在吟游诗人的面前停下来,对奥兰斯笑了笑:“抱歉,出门的时候没有准备派朗,现在能暂借我几枚吗?”
奥兰斯递给我三枚十派朗和两枚五派朗,我出神地盯着上面的头像,千年前把派朗送给西瓜尔的记忆和普瑞尔刚到亚特兰蒂斯的记忆一股脑儿全涌出来。鼻子有些微酸,不确定自己是在伤怀已经流逝的美好岁月,还是在伤感这些年的一事无成。
把硬币全部扔进吟游诗人的帽子里:“劳驾,能换一首歌吗?”
吟游诗人朝我鞠躬:“尊敬的客人,您想要听什么歌呢?”
我犹豫了一下:“……星之所在。”
吟游诗人为难地皱起眉头:“这是一首古老的歌,现在很少有人会唱了。”
是的,很久以前,它曾是国王陛下最爱的曲子……”只是,现在的他可能再也不会听这首我专门为他做的曲子了。
吟游诗人调弄了几下琴弦,不好意思地舔了舔舌头:“这首曲子的主旋律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我可以为您试一试。”
前奏音乐舒缓地响起,在这喧嚣的大街上回荡着:
“调顺的星光像寂静后的一首歌
歌中有你的陪伴
我就无畏明日的天空
夜在沉眠,黎明将至
星空渐渐融入晨光之中
可你的光辉依旧灿烂夺目
善良也好,或是虚伪
不管你是如何,我都想试着去感受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羁绊
像黎明前星空的颜色
任谁也无法抹灭……”
吟游诗人随音乐哼唱着,他的嗓音低沉暗哑,尽管对曲子并不十分熟稔,依然拨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那根弦。
记忆回溯到百年前那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花木扶疏处,水晶八音盒的光晕在亚特拉斯身上一圈一圈散开,像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孤独,把他和整个尘世的喧嚣隔绝开来。
我还在树丛后头猫着腰打量他,他却忽然抬起头来,目视着我的方向。夜空下,他的眼睛熠熠生辉,仿佛银河所有的星星都钻进了那双瞳仁里。
我呼吸一滞。
他缓缓取下银色假面,微卷长发顺着摘下的面具被轻轻地拨到肩膀一边。露出在月光下格外皎白的脸颊,眼窝中深嵌着一对海蓝宝石般的瞳仁,一袭雪白长袍及至脚踝。
夜是黑色的,天空是黑色的,树丛是黑色的,万事万物都是黑色的,只有亚特拉斯周身散发出光晕,仿佛成千上万只看不见的流萤在围绕着他翩翩飞舞。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认真聆听这首曲子时的样子。
可当时身为普瑞尔的种种举动……想起来就觉得好笑,笑完后又是无限的心酸。
……
不等吟游诗人唱完,我就率先离开那里,奥兰斯紧跟在我的身后。
“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奥兰斯不像迦尔,他是一个太过细心的人,说话的时候也尽量斟词酌句:“珀罗普斯殿下,您应该懂得释怀。”
我苦涩地笑了笑:“奥兰斯,他现在还怪我吗?”
“您是说一百年前的事情?”
“嗯……”
“陛下他……刚开始确实很没有办法接受。”奥兰斯冰蓝色眼睛凝望着远处,像是在回忆久远的事情:“在您当众与陛下解除‘永恒的恋人’关系之后,陛下回到亚特兰蒂斯,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把自己关在繁星殿,不吃不喝,不理朝政……可以说我跟着他这么多年,从未见他这样过。”
“后来呢?”我紧张地问。
“我和迦尔去过一次繁星殿,地板上,墙壁上,书桌上,床上,凌乱散放着全是您的画像,那些都是陛下凭记忆为您画的,您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陛下全用画笔记录了下来。”
我不自觉地死死攥紧拳头。
“后来是四王子殿下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劝服陛下。”奥兰斯的目光变得极为悠长,似乎那段过往中有太多艰辛与坎坷不足为外人道,但现在,他已经可以很平静地述说:“陛下把所有画一把火烧了干净,只剩下唯一一幅,被四王子送去黄金大门的底层收藏起来——直到不久前,黄金大门遭窃,那幅画流落去了希腊……”
“我知道了。”我深吸几口气,才勉强镇定下来:“埃泽斯被派去回购那幅画。”
“是的,祭司院一致认为不能让国王陛下的私人物品流落在外,特别是希腊。”奥兰斯礼貌地笑了笑:“其实大多数祭司是认为不应该让您知道这幅画的存在吧!”
我能理解这些祭司的想法,毕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亚特拉斯的“敌人”。
“只有国王陛下认为即使您知道了,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我猜测,或许是他已经放下了,又或是他认为不需要向您隐瞒这一段事实吧。”奥兰斯带着我拐到了一个僻静的街道,喧闹声逐渐远离,显得他的声音格外清亮:“相信您也已经看到了,陛下这些年大肆改革,效果非常显著,亚特兰蒂斯虽然不再信仰诸神却得到了令奥林匹斯都忌惮的发展,陛下让我们坚信:我们即是自己的神。”
我静静地聆听,直到奥兰斯说完。
“奥兰斯,事实真有你说的那么完美无缺吗?”
他震惊地盯着我,但很快,又释然地笑了起来:“从前就听伊菲蒙殿下说过,珀罗普斯殿下有一双看透世事的眼睛。就在刚才,我真正信服了——现在坦诚相告:事实正如您所猜想的,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二王子伽狄鲁斯殿下无缘由地一直和陛下唱反调;六王子奥特库吞殿下是一个保守的学究派,他认为凡事都必须有章可循,陛下这种打破等级的改革没有前例,自然应该反对到底;七王子埃拉西普尤斯殿下一直非常崇拜海神并支持等级制度,是改革的主要反对者;九王子埃泽斯殿下起初很赞同改革税法,但是近几年,陛下主张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加大祭司占有国民比重,以及推广祭司发展缩小等级分化等等举措触及到了九王子的利益,他也成为了反对者之一。”
奥兰斯顿了顿,“总之,现在帝国内部基本算是分为三派,一派维护陛下,一派反对陛下,还有少数像三王子安弗雷斯殿下那样的中间派。”
“看来亚特兰蒂斯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太平。”站在皇家塔罗学院的观星台上,我忧心忡忡地凝视着远处宛如星辰的万家灯火,诚挚地对奥兰斯说:“站在我的立场,实在不应该在亚特兰蒂斯的改革问题上多插嘴,但是,我想你们应该早就预料到今天会发生的一切,并且也想好了相应的对策。”
“是的。”奥兰斯与我并肩而立,拢了拢被风吹开的斗篷:“亚特兰蒂斯还在蓬勃发展,而现在我们目能所及的一切硕果,其实都是殿下您赐予的。”
“旁观者清,其实我知道您为什么会在百年前的奥林匹斯山拒绝陛下。”他目光非常坦白地注视着我:“如果没有您的牺牲,今日的帝国绝不会如此接近一个理想国。”
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被夜风吹走。
“奥兰斯,如果有一天你和迦尔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你会怎么做?”
这个问题似乎难倒了睿智的审判主祭司。
他沉吟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只要他活着,一切都有可能,不是么?”像是松了一口气,他温柔地笑了起来,“殿下比我聪明,必然清楚相同情况下,现在这种是最好的结局……”
是的,也许唯有在目睹眼前满目繁华的烟火人间时,我才能确定,我所做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如今的结局,是最好的……
……
…………
和奥兰斯告别后,我离开了皇家塔罗学院,走到暌违已久的皇家能源学院。奥兰斯告诉我,亚特拉斯这百年间都有在秘墙给我留言。循着记忆中的路线,我很快就找到了那堵爬满藤蔓的矮墙,右手轻轻扶着墙面,我发现自己念咒语时的声音居然在颤抖。
长长的咒语结束,面前的墙消失了。
魔力幻化的银色雪花在我身边飘舞,一排排数字从眼前飘过,这是以亚特兰蒂斯年记载的日期。
伸出手指轻轻触碰一个,是亚特拉斯最近的留言,一年前:
“今天刚刚得知,一个承载着我血脉的小生命正在孕育着,九个月以后就要降临人间了。珀罗普斯,说真的,我不知道自己此刻是什么心情,就只是想先告诉你。”
留言不长,我点开再前面一个,亚特兰蒂斯1578年,距今二十年:
“今天,我的书记官琼纳斯永远地阖上了眼睛。他与我共事了两百年,我以为已经习惯见证人类的生老病死,却原来依然还是无法战胜死亡的恐惧。想到亚特兰蒂斯,想到我们一直追寻的公正与自由,如果没有人在我死后依然为之奋斗,我又怎么能甘心去赴死?
珀罗普斯,对不起,我想我会做出一个让你痛彻心扉的决定。
但是……我不会忘记,无论呼吸或死亡,永不背弃彼此,以爱之名。”
双手紧紧地捂住嘴巴,我克制了很久,几乎用尽生平所有的力气,才点开再前一封留言,亚特兰蒂斯1528年,距今七十年:
“今天神王又把你派去特尔斐做神谕,你肯定不知道我混迹在人群中偷偷凝望你……我想这将是最后一次了。”
再前一个,亚特兰蒂斯1527年,距今七十一年:
“今天照例去特尔斐看你做神谕,一月一度。迦尔已不耐烦陪我来,我只能独自前去,你好像瘦了些。”
再前一个,亚特兰蒂斯1505年,距今九十三年:
“今天是你苏醒后第一次在人间做神谕,你说:‘与众神的信仰将是救赎自身灵魂的唯一道路。’我真想走到你面前对你说:‘你才是救赎我的唯一道路’。在此之前,珀罗普斯,我试想过无数可以拥有你的办法,甚至可以向众神低头,为了你,为了亚特兰蒂斯。”
再前面一个,亚特兰蒂斯1498年,距今一百年:
“今天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情:一个连命运线都要靠别人纺织的人根本什么都给不了你。珀罗普斯,或许你的拒绝是对的……”
读过的留言很快随纷飞雪花消逝,快到令我来不及伸手抓住,就已经消散在指间……
我眼前只剩下最后一个,日期是亚特兰蒂斯1497年,我们缔结永恒恋人的那一年:
“今天我要带普瑞尔去歌菲亚海滩,准备给他讲诉我爱上你的瞬间。这将意味着我终于决定抛开一切和普瑞尔在一起,这一次,神也不能将我们分开……你能感受到吗,珀罗普斯,我现在很幸福。”
亚特拉斯轻快又动听的尾音回荡着,渐渐地,渐渐地,消散在冰冷的墙缝中。
魔力失效,一切被打回原形。
我把脸紧紧贴在冰冷的秘墙上,仿佛贴着爱人温热的侧脸那样,轻轻闭上眼睛:“嗯,亚特拉斯,我也……很幸福……”
作者有话要说:
这一章又戳我泪点了……我泪点好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