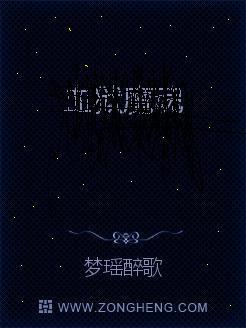第42章
(美)卡勒德·胡赛尼提示您:看后求收藏(飞飞小说网www.wonderlifelive.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如果说白沙瓦让我回忆起喀布尔过去的光景,那么,伊斯兰堡就是喀布尔将来可能成为的城市。街道比白沙瓦的要宽,也更整洁,种着成排的木槿和凤凰树。市集更有秩序,而且也没有那么多行人和黄包车挡道。屋宇也更美观,更摩登,我还见到一些公园,林阴之下有蔷薇和茉莉盛开。
法里德在一条通往玛加拉山的巷道找了个小旅馆。路上,我们经过著名的费萨尔清真寺,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香火甚旺,耸立着巨大的水泥柱和直插云霄的尖塔。看到清真寺,索拉博神色一振,趴在车窗上,一直看着它,直到法里德开车拐了个弯。
旅馆的房间比我和法里德在喀布尔住过那间好得太多了。被褥很干净,地毯用吸尘器吸过,卫生间没有污迹,里面有洗发水、香皂、刮胡刀、浴缸,有散发着柠檬香味的毛巾。墙上没有血迹。还有,两张单人床前面的柜子上摆着个电视机。
“看!”我对索拉博说。我用手将它打开——没有遥控器,转动旋钮。我调到一个儿童节目,两只毛茸茸的卡通绵羊唱着乌尔都语歌曲。索拉博坐在床上,膝盖抵着胸膛。他看得入迷,绿眼珠反射出电视机里面的影像,前后晃动身子。我想起有一次,我承诺哈桑,在我们长大之后,要给他家里买台彩电。
“我要走了,阿米尔老爷。”法里德说。
“留下过夜吧,”我说,“路途遥远。明天再走。”
“谢谢你。”他说,“但我想今晚就回去。我想念我的孩子。”他走出房间,在门口停下来。“再见,亲爱的索拉博。”他说。他等着回应,但索拉博没理他,自顾摇着身子,屏幕上闪动的图像在他脸上投下银光。
在门外,我给他一个信封。打开之后,他张大了口。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我说,“你帮了我这么多。”
“这里面有多少钱?”法里德有点手足无措。
“将近两千美元。”
“两千……”他说,下唇稍微有点颤抖。稍后,他驶离停车道的时候,揿了两下喇叭,摇摇手。我也朝他招手。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回到旅馆房间,发现索拉博躺在床上,身子弯成弓形。他双眼合上,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睡着了。他关掉了电视。我坐在床上,痛得龇牙咧嘴,抹去额头上的冷汗。我在想,要过多久,起身、坐下、在床上翻身才不会发痛呢?我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吃固体食物呢?我在想,我该拿这个躺在床上的受伤的小男孩怎么办?不过我心里已经有了想法。
柜台上有个饮水机。我倒了一玻璃杯水,吞下两片阿曼德的药丸。水是温的,带有苦味。我拉上窗帘,慢慢躺在床上。我觉得自己的胸膛会裂开。等到痛楚稍减、我又能呼吸的时候,我拉过毛毯盖在身上,等着阿曼德的药丸生效。醒来之后,房间变黑了。窗帘之间露出一线天光,那是即将转入黑夜的紫色斜晖。汗水浸透被褥,我脑袋昏重。我又做梦了,但忘记梦到什么。
我望向索拉博的床,发现它是空的,心里一沉。我叫他的名字,发出的嗓音吓了自己一跳。那真是茫然失措,坐在阴暗的旅馆房间,离家万里,身体伤痕累累,呼唤着一个几天前才遇到的男孩的名字。我又喊了他的名字,没听到回答。我挣扎着起床,查看卫生间,朝外面那条狭窄的走廊望去。他不见了。
我锁上房门,一只手扶在走廊的栏杆上,跌跌撞撞走到大堂的经理办公室。大堂的角落有株满是尘灰的假棕榈树,粉红的火烈鸟在壁纸上飞舞。我在塑料贴面的登记柜台后面,找到正在看报纸的经理。我向他描绘索拉博的样子,问他有没有见到过。他放下报纸,摘掉老花镜。他的头发油腻,整齐的小胡子有些灰白,身上依稀有种我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水果味道。
“男孩嘛,他们总喜欢出去玩。”他叹气说,“我有三个男孩,他们整天都跑得不见踪影,给他们母亲惹麻烦。”他用报纸扇风,看着我的下巴。
“我认为他不是出去玩,”我说,“我们不是本地人,我担心他会迷路。”
他摇摇头:“你应该看好那个男孩,先生。”
“我知道,”我说,“但我睡着了,醒来他已经不见了。”
“男孩应该多加关心的,你知道。”
“是的。”我说,血气上涌。他怎么可以对我的焦急如此无动于衷?他把报纸交在另外一只手上,继续扇风,“他们现在想要自行车。”
“谁?”
“我的孩子。”他说,“他们总在说:‘爸爸,爸爸,请给我们买自行车,我们不会给你带来麻烦。求求你,爸爸。’”他哼笑一声,“自行车。他们的母亲会杀了我,我敢向你保证。”
我想像着索拉博横尸街头,或者在某辆轿车的后厢里面,手脚被绑,嘴巴被塞住。我不想他死在我手里,不想他也因我而死。“麻烦你……”我说,皱起眉头,看见他那件短袖蓝色棉衬衫翻领上的商标,“费亚兹先生,你见过他吗?”
“那个男孩?”
我强忍怒火:“对,那个男孩!那个跟我一起来的男孩。以真主的名义,你见过他吗?”
扇风停止。他眼睛一缩:“别跟我来这套,老弟,把他弄丢的不是我。”
虽然他说得没错,但不能平息我的怒火。“你对,我错了,是我的错。那么,你见过他吗?”
“对不起。”他强硬地说,戴上眼镜,打开报纸,“我没见过这样的男孩。”
我在柜台站了一会,抑制自己别发火。我走出大厅的时候,他说:“有没有想过他会去什么地方?”
“没有。”我说。我感到疲惫,又累又怕。
“他有什么爱好吗?”他说,我看见他把报纸收起来。“比如说我的孩子,他们无论如何总是要看美国动作片,特别是那个阿诺什么辛格演的……”
“清真寺!”我说,“大清真寺。”我记得我们路过的时候,清真寺让索拉博从委靡中振奋起来,记得他趴在车窗望着它的样子。
“费萨尔?”
“是的,你能送我去吗?”
“你知不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他问。
“不知道,可是……”
“光是它的院子就可以容下四万人。”
“你能送我到那边去吗?”
“那儿距这里还不到一公里。”他说,不过他已经从柜台站起来。
“我会付你车钱。”
他叹气,摇摇头,“在这里等着。”他走进里间,出来的时候换了一副眼镜,手里拿着串钥匙,有个披着橙色纱丽的矮胖女人跟在身后。她坐上他在柜台后面的位子。“我不会收你的钱。”他朝我吹着气,“我会载你去,因为我跟你一样,也是个父亲。”
我原以为我们会在城里四处寻找,直到夜幕降临。我以为我会看到自己报警,在费亚兹同情的目光下,给他们描绘索拉博的样子。我以为会听见那个警官疲累冷漠的声音,例行公事的提问。而在那些正式的问题之后,会来个私人的问题:不就是又一个死掉的阿富汗孩子,谁他妈的关心啊?
但我们在离清真寺约莫一百米的地方找到他,坐在车辆停满一半的停车场里面,一片草堆上。费亚兹在那片草堆停下,让我下车。“我得回去。”他说。
“好的。我们会走回去。”我说,“谢谢你,费亚兹先生,真的谢谢。”
我走出去的时候,他身子从前座探出来。“我能对你说几句吗?”
“当然。”
在薄暮的黑暗中,他的脸只剩下一对反照出微光的眼镜。“你们阿富汗的事情……这么说吧,你们有点鲁莽。”
我很累,很痛。我的下巴抖动,胸膛和腹部那些该死的伤口像鱼钩在拉我的皮肤。但尽管这样,我还是开始大笑起来。
“我……我说了……”费亚兹在说话,但我那时哈哈大笑,喉头爆发出来的笑声从我缝着线的嘴巴迸出来。
“疯掉了。”他说。他踩下油门,车轮在地面打转,尾灯在黯淡的夜光中闪闪发亮。
“你把我吓坏了。”我说。我在他身旁坐下,强忍弯腰带来的剧痛。
他望着清真寺。费萨尔清真寺的外观像一顶巨大的帐篷。轿车进进出出,穿着白衣的信徒川流不息。我们默默坐着,我斜倚着树,索拉博挨着我,膝盖抵在胸前。我们听着宣告祈祷开始的钟声,看着那屋宇随日光消退而亮起成千上万的灯光。清真寺在黑暗中像钻石那样闪着光芒。它照亮了夜空,照亮了索拉博的脸庞。
“你去过马扎里沙里夫吗?”索拉博说,下巴放在膝盖上。
“很久以前去过,我不太记得了。”
“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带我去过那儿,妈妈和莎莎也去了。爸爸在市集给我买了一只猴子。不是真的那种,而是你得把它吹起来的那种。它是棕色的,还打着蝴蝶结。”
“我小时候似乎也有一只。”
“爸爸带我去蓝色清真寺。”索拉博说,“我记得那儿有很多鸽子,在那个回教堂外面,它们不怕人。它们朝我们走来,莎莎给我一小片馕,我喂那些鸟儿。很快,那些鸽子都围在我身边咯咯叫。真好玩。”
“你一定很想念你的父母。”我说。我在想他有没有看到塔利班将他的父母拖到街上。我希望他没有。
“你想念你的父母吗?”他问,把脸颊放在膝盖上,抬眼看着我。
“我想念我的父母吗?嗯,我从没见过我的妈妈。我爸爸几年前死了,是的,我想念他。有时很想。”
“你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我想起爸爸粗壮的脖子,黑色的眼睛,那头不羁的棕发,坐在他大腿上跟坐在树干上一样。“我记得他长什么样子,”我说,“我还记得他身上的味道。”
“我开始忘记他们的面孔,”索拉博说,“这很糟吗?”
“不,”我说,“是时间让你忘记的。”我想起某些东西。我翻开外套的前袋,找出那张哈桑和索拉博的宝丽莱合影,“给你。”
他将相片放在面前几英寸的地方,转了一下,以便让清真寺的灯光照在上面。他久久看着它。我想他也许会哭,但他只是双手拿着照片,拇指在它上面抚摸着。我想起一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来的话,或者是从别人口里听来的:阿富汗有很多儿童,但没有童年。他伸出手,把它递给我。
“你留着吧,”我说,“它是你的。”
“谢谢你。”他又看了看照片,把它放在背心的口袋里面。一辆马车发着声响驶进停车场。马脖子上挂着很多小铃铛,随着马步叮当作响。
“我最近经常想起清真寺。”索拉博说。
“真的吗?都想些什么呢?”
他耸耸肩,“就是想想而已。”他仰起脸,看着我的眼睛。这时,他哭了起来,轻柔地,默默地。“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阿米尔老爷?”
“当然。”
“真主会不会……”他开始说,语声有点哽咽,“真主会不会因为我对那个人做的事情让我下地狱?”
我伸手去碰他,他身子退缩。我收回手。“不会,当然不会。”我说。我想把他拉近,抱着他,告诉他世界曾经对他不仁,他别无选择。
他的脸扭曲绷紧,试图保持平静:“爸爸常说,甚至连伤害坏人也是不对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还因为坏人有时也会变好。”
“不一定的,索拉博。”
他疑惑地看着我。
“那个伤害你的人,我认识他很多年。”我说,“我想这个你从我和他的对话中听出来了。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他……他有一次想伤害我,但你父亲救了我。你父亲非常勇敢,他总是替我解决麻烦,为我挺身而出。所以有一天那个坏人伤害了你父亲,他伤得你父亲很重,而我……我不能像你父亲救过我那样救他。”
“为什么人们总是伤害我父亲?”索拉博有点喘着气说,“他从不针对任何人。”
“你说得对。你父亲是个好人。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亲爱的索拉博,这个世界有坏人,有时坏人坏得很彻底,有时你不得不反抗他们。你对那个人所做的,我很多年前就应该对他做的。他是罪有应得,甚至还应该得到更多的报应。”
“你觉得爸爸会对我失望吗?”
“我知道他不会。”我说,“你在喀布尔救了我的命。我知道他会为你感到非常骄傲。”
他用衣袖擦脸,弄破了他嘴唇上挂着的唾液泡泡。他把脸埋在手里,哭了很久才重新说话。“我想念爸爸,也想念妈妈,”他哽咽说,“我想念莎莎和拉辛汗。但有时我很高兴他们不……他们不在了。”
“为什么?”我碰碰他的手臂,他抽开。
“因为……”他抽泣着说,“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我这么脏。”他深吸一口气,然后抽泣着慢慢呼出,“我很脏,浑身是罪。”
“你不脏,索拉博。”我说。
“那些男人……”
“你一点都不脏。”
“……他们对我……那个坏人和其他两个……他们对我……对我做了某些事情。”
“你不脏,你身上没有罪。”我又去碰他的手臂,他抽开。我再伸出手,轻轻地将他拉近。“我不会伤害你,”我低声说,“我保证。”他挣扎了一下,全身放松,让我将他拉近,把头靠在我胸膛上。他小小的身体在我怀里随着每声啜泣抽动。
喝着同样的奶水长大的人之间会有亲情。如今,就在这个男孩痛苦的泪水浸湿我的衣裳时,我看到我们身上也有亲情开始生长出来。在那间房间里面和阿塞夫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开。
我一直在寻找恰当的机会、恰当的时间,问出那个萦绕在我脑里、让我彻夜无眠的问题。我决定现在就问,就在此地,就在此刻,就在照射着我们的真主房间的蓝色灯光之下。
“你愿意到美国去、跟我和我的妻子一起生活吗?”
他没有回答,他的泪水流进我的衬衣,我随他去。
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两个都没提起我所问过他的,似乎那个问题从来没被说出来。接着某天,我和索拉博坐出租车,前往“达曼尼科”——它的意思是“那座山的边缘”——观景台。它坐落在玛加拉山半腰,可以看到伊斯兰堡的全景,树木夹道的纵横街路,还有白色房子。司机告诉我们,从上面能看到总统的宫殿。“如果刚下过雨,空气清新,你们甚至能看到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伊斯兰堡附近古城】。”他说。我从他那边的观后镜,看见他扫视着我和索拉博,来回看个不停。我也看到自己的脸,不像过去那样浮肿,但各处消退中的淤伤在它上面留下黄色的痕迹。
我们坐在橡胶树的阴影里面,野餐区的长椅上。那天很暖和,太阳高悬在澄蓝的天空中,旁边的长椅上坐着几个家庭,在吃土豆饼和炸蔬菜饼。不知何处传来收音机播放印度音乐的声音,我想我在某部旧电影里面听过,也许是《纯洁》【Pakeeza,1971年公映,巴基斯坦电影】吧。一些孩子追逐着足球,他们多数跟索拉博差不多年纪,咯咯发笑,大声叫喊。我想起卡德察区那个恤孤院,想起在察曼的办公室,那只老鼠从我双脚之间穿过。我心口发紧,猛然升起一阵始料不及的怒火,为着我的同胞正在摧毁他们的家园。
“怎么了?”索拉博问。我挤出笑脸,跟他说没什么。
我们把一条从旅馆卫生间取来的浴巾铺在野餐桌上,在它上面玩起番吉帕。在那儿跟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一起玩牌,温暖的阳光照射在我脖子后面,那感觉真好。那首歌结束了,另外一首响起,我没听过。
“看。”索拉博说,他用扑克牌指着天空。我抬头,见到有只苍鹰在一望无垠的天空中翱翔。
“我还不知道伊斯兰堡有老鹰呢。”
“我也不知道。”他说,眼睛看着那只回旋的鸟儿,“你生活的地方有老鹰吗?”
“旧金山?我想有吧,不过我没有见过很多。”
“哦。”他说。我希望他会多问几句,但他又甩出一手牌,问是不是可以吃东西了。我打开纸袋,给他肉丸夹饼。我的午餐是一杯混合的香蕉汁和橙汁——那个星期我租了费亚兹太太的榨汁机。我用吸管吮着,满嘴甜甜的混合果汁。有些从嘴角流出来,索拉博递给我一张纸巾,看着我擦嘴唇。我朝他微笑,他也微笑。
“你父亲跟我是兄弟。”我说,自然而然地。在我们坐在清真寺附近那晚,我本来打算告诉他,但终究没说出口。可是他有权利知道,我不想再隐瞒什么事情了。“同父异母,真的。我们有共同的爸爸。”
索拉博不再吃东西了,把夹饼放下,“爸爸没说过他有兄弟。”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为什么不知道?”
“没人告诉他,”我说,“也没人告诉我。我最近才发现。”
索拉博眨眼,好像那是他第一次看着我,第一次真正看着我。“可是人们为什么瞒着爸爸和你呢?”
“你知道吗,那天我也问了这个问题。那儿有个答案,但不是个好答案。让我们这么说吧,人们瞒着我们,因为你父亲和我……我们不应该被当成兄弟。”
“因为他是哈扎拉人吗?”